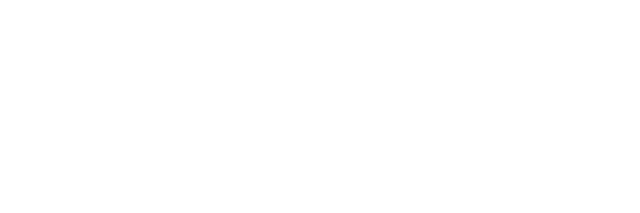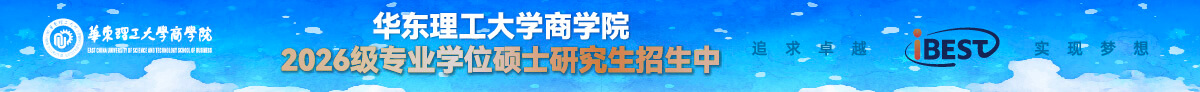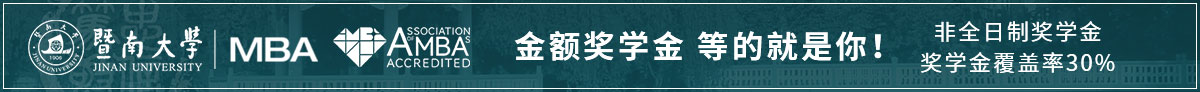唐藝
2020級清華全球MBA
巴黎高等商學院 (HEC)
雙學位項目在讀
這是我第一次踏入這個國家,在這里從字母表開始學習法語。
01
勘極而成知
相較于很多歐洲高校傳統嚴肅的學風,巴黎高等商學院給MBA學生們釋出了更多的選擇空間,雙學位這九個月的學習幾乎是定制化的——專業課、任選課、證書課程。現在是我來這里的第六個月,專業課已結束,任選課進行到一半。
第一學期的專業課,我在7個專業中選擇了戰略市場營銷方向。這是一個規模相對不大、口碑和反饋卻不錯的專業,它在課程設置中將理論和實踐、創造性與實用性結合得很好。
基礎課程“高級市場營銷學”的教授、市場營銷專業的學術負責人安勞·賽麗爾老師,是一位很有法式風格的優雅女士,也是社會和認知心理學領域的專家,學校里有不少人因她的人格魅力和學術造詣而成為她的小粉絲。而她本人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內曼的擁躉,于是在她的影響下,卡內曼受邀來到巴黎高商講座的時候,我們全班幾乎都早早去到禮堂占座。聽賽麗爾教授講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因為她本身就從事創造力相關的研究,每一堂課她都致力于推倒我們思維里那個把認知和真實的世界隔開的“墻”,激發創造力和批判性思考。“如何讓全班同學吃蟑螂”“如何通過去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重新發明教室”——市場營銷中的影響力、價值創造這些重要概念就在她的課上用一場場極端的思想實驗傳遞給我們——實際上,如果不是因為疫情下嚴格的行政管理,她第一個想推倒的就是教室真實的墻:“在這么好的天氣里被困在教室上課實在是太荒唐了,今天我講的一切本該可以是我們穿上外套走在校園里,在去往湖邊的路上討論的。”
相較于高級市場營銷學的思想實驗和案例教學,數字化營銷課似乎更具實踐性。我們需要選擇一個感興趣的行業并構想自己的產品原型,然后在六周的時間里使用全套的數字化營銷武器去推廣它——建立網頁、關鍵字優化、社交媒體、搜索引擎廣告、電子郵件營銷等等——一場相當沉浸的線上營銷經理的體驗,以至于當結課時收到教授的郵件說,現在項目已經結束,你可以注銷社交賬戶、禁用產品網頁、恢復正常生活的時候,幾乎有些感動和不舍。整個實踐過程中,對我來說最有趣也最有收獲的就是去發現中西的差異與統一,連教授也會在課上坦言五六年前當來自中國的同學向他介紹Tik Tok,并保證這個平臺一定會火時,他內心是不相信的,而現在他甚至相信Tik Tok的信息流比他更懂自己。同樣的,來這里之前我對推特和臉書少有接觸,也幾乎不會留意郵件營銷。這些激烈的變化與融合也許就是數字化營銷的魅力所在。在實踐操作中,我得以拉開時間的維度去觀察和對比,思考我們與西方在各個營銷方式上的發展階段和手法,常常會發現我們互為過去和未來。
不多贅述,三個月的專業課學習非常緊湊充實,項目實踐之下有理論學習,理論之下有R語言、SPSS、Mailchimp等等的工具支持,在實踐中這些理論和工具都逐漸具體好用起來。
02
意氣與天下相期
幾個月前,我向HEC雙學位的學長耿代濤請教經驗,在他給我的建議中,有一句我時常會想起:“你要越多元,你內生出來的才越準確。”
在所有我采訪過的校友和同學口中,HEC最常被人稱道、幾乎毋庸置疑的特點就是它的文化多樣性,這是從一踏進校園就能感知到的。文化與文化各自存在著,有時交匯,或許融合,或許碰撞,沒有一種可以占主導。
前面提到過我的專業規模不大,我們只有17個人,但大家的背景和故事千差萬別,因此課堂上常常能感受到不同性別、國籍、工作背景之間,文理科思維方式之間,甚至是有沒有當過父母的不同心態之間碰撞出的火花。這些討論在市場營銷這樣一個以人為本的專業似乎更加被珍惜和重視。課下我們還能聽印度同學講他們的戒指與占星學,聽瑞典同學講森林軼事,聽法國同學介紹奶酪和酒,當然我也會將他們對中國的那些好奇講給他們聽。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我自覺初來乍到,但彼時這里的同學們也多是剛剛從疫情期間一個學期的強制線上課程中被釋放出來,與彼此“網友見面”,我的期待和他們的熱情幸運地撞了個正著。
如果說同樣的專業還是集結了一群有相似之處的人的話,那么任選課就是更精彩的辯論場。我們會為了配置一個虛擬的投資組合因投資理念不同吵得不可開交,然后還要想辦法達成團隊統一;會有同學在課上向老師當面坦言你這一套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上并不合理;我們拿著九十年代的大部頭論文研究其中的東西方消費心理差異,竟然發現其中對當下的適用性;席間會有其他國家的同學直白地提問該如何理解我們的國潮回歸,討論中竟然也給了我新的視角。
我還加入了卡地亞與巴黎高商、歐洲高商共同成立的“轉折點”研究委員會,每個月一到兩次,我們會與來自這兩所商學院的同學,以及來自全世界各地卡地亞內部的同事們開會討論Z世代如何看待那些重要但又似乎沒有被充分討論的議題——愛、性別、成功等等。
在與卡地亞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西里爾·維格納的討論會上,當我們談到Z世代的自我意識、自我表達、對刻板印象的打破時,維格納先生說道:“對比30年前,我看到了在一些方面人們減少了刻板印象,但某些角度上刻板印象卻在增加。《星球大戰》的第一集,男主角盧克·天行者就是那種典型的少年英雄形象,很坦誠、很瘦、沒有那么多肌肉。而在最新一集的《星球大戰》,我們看到年輕的男性英雄都肌肉發達,女性英雄也身材性感,可以看出明顯的審美轉變。在韓國,整容手術從未像今天這樣流行,在迪拜有一條大街上到處都是整形外科診所。越來越多的人在改變自己以成為另外一個人、成為刻板印象。”
觀點資訊之外,那些來自其他文化的個性表達、處事方式也都是打磨和尋找自己的養料。在這里我得以打破幻想,以多元的視角考慮當下的問題,也找到了嶄新的職業興趣和方向。也許就如代濤學長所說,它們幫助我內生出更準確的自我。
03
觸物皆有會心處
除了學習和求職,你可以感受到這里有一種氛圍叫做把校園生活的每一個面過得“煞有介事”。
在迎新晚會上,有人集合小半個班排演晦澀難懂的意識流短劇,有人用九成觀眾聽不懂的母語朗誦6分鐘詩歌;在社團活動周,我們五天走訪了巴黎13個奢侈品企業;學生會和社團的換屆選舉比出了迷你聯合國的味道;不論天氣有多冷,每周總有那么一兩天宿舍樓下的長椅和草坪上有派對的笑聲和歌聲到天明。
我想留學的迷人和特別之處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場萬里路和萬卷書兼得的冒險。我很感恩學校和家人的支持,也很慶幸我的留學發生在這個年齡,讓我能為在固定的環境和領域中不自覺陷入舒適圈的自我打開了認知的一扇天窗。雖然一扇窗戶只能朝向一個方向,但它已經提供了足夠我吸收和碰撞的“多樣性”;也讓我能在近距離面對起這些由于多樣而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少數”和“真實”時——西方世界對亞洲和中國的不理解、不尊重,被反復討論依然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發生在校園的惡性事件等等——不驚慌、不迷失。
我想我會很愛這些瞬間:去洗衣房的路上,在森林里跟一只咕咕鳥相遇;在云彩很好看的湖邊等到日落;在舞房里猜著老師口令的意思,邊偷眼看同學邊笨拙地擺弄姿勢;在超市自助秤前,因為沒分清洋蔥、大蔥和韭蔥的叫法而灰頭土臉地貼錯標簽;在國內早已是深夜的晚上,數著窗外的飛機拉線狠狠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