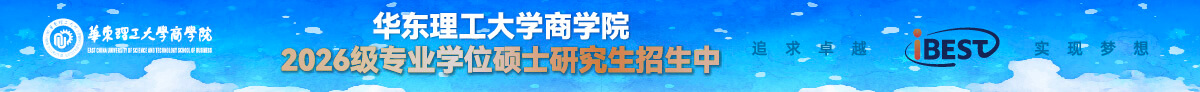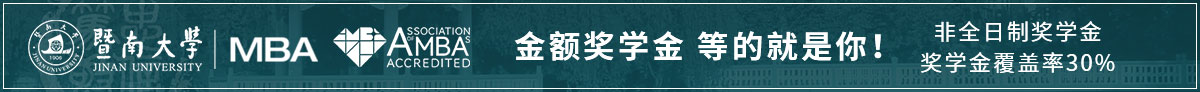白長虹,教授、博士生導師,《南開管理評論》主編,現(xiàn)任南開大學商學院院長。
管理學者的倫理責任
現(xiàn)代科技賦予了人類支配世界的強大力量,科技成果及其產(chǎn)品已經(jīng)遍布世界每個角落,它們的影響還會隨著時間一代代累積,反復疊加并持續(xù)下去。如果這樣的力量被濫用,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即使不是惡意濫用,許多科技成果仍然有長期的、難以預料的作用。人類應該如何約束自己,如何與我們所在的地球家園休戚與共,成為了一個嚴肅的議題。在20世紀70年代,圍繞這一議題出現(xiàn)了兩個重要的理念,一是為人熟知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觀,一是漢斯·約納斯的“責任倫理”觀。“責任倫理”的概念最早為馬克斯·韋伯提出,他把倫理分為“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前者是指源自信仰的善惡觀,后者則強調(diào)人們要對其行動的后果負責。約納斯則認為,既然人類掌握的科技力量可能會傷害這個世界,就必須用責任倫理加以約束。也就是說,科技工作者的責任不僅僅是發(fā)明或發(fā)現(xiàn)什么事物,還牽涉到這些發(fā)明或發(fā)現(xiàn)的可能后果。
現(xiàn)代科技拓展了可知的時空邊界,也促使人們在更大的時空范圍內(nèi)追問科技活動的意義,而不滿足于僅僅用善良意志去解釋這些活動的初衷。約納斯正是在這樣的視域中審視著科技活動。他指出,當人類具有了改變自然的力量,一些科技活動的后效會影響到子孫萬代時,就不能“漠然地同人以外的生命世界打交道,也不能漠然地和人自身打交道”,而應該承擔起對自然和未來人類存在的整體性責任。人類與自然的長遠存在和對未來生命的尊重,構(gòu)成了責任倫理觀的核心。約納斯還對醫(yī)學人體試驗、克隆技術(shù)等引發(fā)的倫理問題進行了探討,讓人認識到責任倫理并不是夢中囈語,而是對現(xiàn)實問題的警覺,特別是當人成為科技的對象時,必須對可能導致惡果的活動加以限制。
約納斯的“責任倫理”理論,代表了生活在科技時代的人們反思科技活動的一種思潮。他的著作《責任原理》一書出版后,立即在學界引起了熱烈反響。雖然一些學者對他反對“人類中心論”的觀點、對“責任倫理”的可實現(xiàn)性有著不同認識,但對于必須防范科技活動的不良后果,卻已是大多數(shù)人的共識。1989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第二次“科學與文化”會議上,與會科學家簽署了《關(guān)于21世紀生存的溫哥華宣言》。宣言中明確寫道,“地球的生存已成為人們所關(guān)心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問題,……造成我們今天這些困難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科學上的進步”。宣言特別強調(diào),為了防止信息學、生物技術(shù)和遺傳工程諸方面的進步在未來產(chǎn)生無可挽回的不良影響,必須將“科學與文化結(jié)合成一體,闡明生存的意義”。
隨著這種責任意識逐漸深入人心,不僅生物醫(yī)學、基因工程等領域組建起了負責監(jiān)管研究活動的、各種級別的倫理委員會,有關(guān)科技創(chuàng)新的社會責任也成為重要的政策議題。在2014年啟動的歐盟《地平線2020計劃》中,列有專項計劃以建立科學和社會之間的有效合作,招募和培養(yǎng)具有社會意識和責任感的科研人才,推進“負責任研究與創(chuàng)新”。而對“負責任研究與創(chuàng)新”這一概念的簡單解釋,就是通過對科學和創(chuàng)新的集體管理來關(guān)注未來。
令人鼓舞的是,管理學領域已有學者呼吁開展負責任的學術(shù)研究,使商學院能夠以更嚴謹、更切題的方式探索對管理實踐有用的可靠知識。只是他們所倡導的倫理觀仍然是一般意義上的學術(shù)道德標準,或者說做一名好科學家所應遵循的行為規(guī)范。約納斯將這種倫理觀稱為“區(qū)域倫理學”。他指出,科技倫理問題“不再是一個好的或壞的科學的問題,而是科學的好的或壞的作用問題”,這句話對于管理學者同樣適用。由于現(xiàn)代科技的交叉發(fā)展,科研的對象、科研方法以及科研成果的使用都比以往更為復雜,從約納斯的責任倫理觀來看,管理學者也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
第一,樹立起更強烈的責任倫理意識,在參與現(xiàn)代科技發(fā)展相關(guān)的課題時,至少要知曉包括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大數(shù)據(jù)、納米技術(shù)等前沿科技已經(jīng)引發(fā)的倫理問題,從有利于人類長期發(fā)展和自然長遠存在的立場上,對這些問題做出獨立判斷,以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
第二,努力選擇有重要理論意義或現(xiàn)實意義的題目進行研究,而不能僅僅根據(jù)個人愛好進行選題。切忌那些對管理理論貢獻不大,研究結(jié)果卻容易被濫用的題目,譬如研究人的種族、相貌特征或宗教信仰與企業(yè)績效的關(guān)系,須知在多樣化價值觀日益盛行的今天,這種研究不大可能揭示企業(yè)運行的真正機理。
第三,在研究過程中對研究對象或研究參與者負責。要從歷史上一些著名研究案例的倫理爭議中汲取教訓,如耶魯大學的“服從權(quán)威”心理實驗、斯坦福大學的“斯坦福監(jiān)獄實驗”以及所謂的“茶室交易”調(diào)查,都曾因為損害受訪者或參與試驗者的利益而引起爭端。特別需要指出,當前有些學者僅是貪圖方便,讓在校學生參加一些心理實驗,而不考慮參加實驗對學生的長期影響,這種行為是有違學術(shù)倫理的。
第四,要維護理論體系的嚴謹性和簡潔性,對后來的學者和企業(yè)界人士負責。學者們應該以嚴謹?shù)膽B(tài)度,努力保持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論架構(gòu)的基本含義,如無必要,勿為之增添新的含義,以便于學者們之間的交流和理論的傳播。如果有些概念或理論已被不同的解釋所“阻塞”,為了管理理論的正常發(fā)展,那些有影響力的學者應該承擔起“疏通”之責。
第五,積極參與“負責任的研究與創(chuàng)新”的管理方法、管理體制和新型創(chuàng)新模式的研究。鑒于相關(guān)研究剛剛起步,雖然國內(nèi)已有學者開始了學術(shù)探索,但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對許多問題的學理性探討還不夠深入,研究成果還不足以支撐起我國這樣一個科技創(chuàng)新大國的科技創(chuàng)新活動。但這也預示著,管理學者在這一領域大有可為。
以健康的管理研究促成管理學的健康發(fā)展,這才是管理學者應該承擔的基本責任!
原文刊發(fā)于《南開管理評論》2021年第六期